古诗文名句赏析:人定亦能胜天,天定亦能胜人
人定胜天,是国人熟知的一个成语,指人的智慧和力量,能够克服自然阻碍,改造环境。在上世纪中叶,领导人面对一穷二白的实际,用人定胜天及战天斗地的精神,激励了无数人投身于建设。可能自那以后,人一定能战胜天(天命)成为了人定胜天的唯一含义。但是,与“人定胜天”相关的语句,自古就有,而且其含义是很丰富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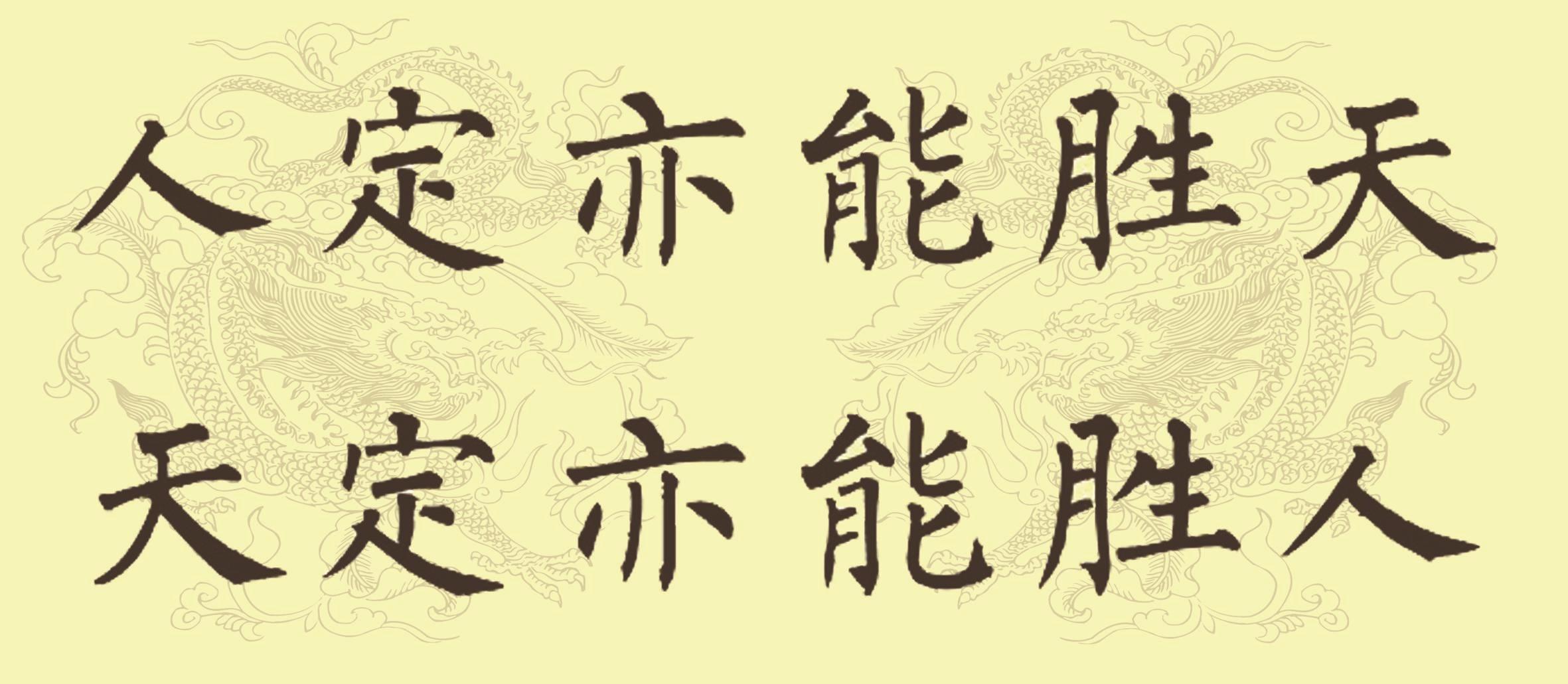
今天所说的“人定亦能胜天,天定亦能胜人”语出金·刘祁所著《归潜志》第十二卷:“传曰,‘人定亦能胜天,天定亦能胜人’,余尝疑之。试以严冬在大厦中独立,悽淡(万态)不能久居。然忽有外人共笑,则殊煖燠,尽人气胜也。因是以思,谓人胜天亦有此理。岂特是哉?深冬执爨或厚衣重衾亦不寒,夏暑居高楼,以冰环坐而加之以扇亦不甚热,大抵有势力者能不为造物所欺,然所以有势力者亦造物所使也。”
这一段,除去中间论证的部分,引者常用“人定亦能胜天,天定亦能胜人”一句,或“人定亦能胜天,天定亦能胜人……大抵有势力者,能不为造物所欺;然所以有势力者,亦造物所使也。”(按:造物,旧时以为万物是天造的,故称天为造物。)刘祁此段文字,如果单独引用“人定亦能胜天,天定亦能胜人”,则很容易曲解其义,因为后面说的很明白:人有势力者能不被天所欺,但这个“势力”其实是天给的。
“人胜天”或“天胜人”之语,由来已久。究其源,《逸周书·文传》中说:“兵强胜人,人强胜天。”太史公所著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借申包胥之口说:“吾闻之,人众者胜天,天定亦能破人。”(申包胥说“吾闻之”,也就是说这话在他之前就已经有所流传了,时间应更早。)唐刘禹锡在《天论》中说:“天非务胜乎人者也,何哉?人不宰则归乎天也。人诚务胜乎天者也,何哉?天无私,故人可务乎胜也。”
而白居易在《策林·辨水旱之灾明存救之术》中,对“人强胜天”的理解,是把握天的规律,顺乎天而行,而非“战胜自然”也。刘禹锡在《天论》中提出的观点也十分重要:“大凡入形器者,皆有能有不能。天,有形之大者也;人,动物之尤者也。天之能,人固不能也;人之能,天亦有所不能也。故余曰:天与人交相胜耳。”
此后,苏轼在《三槐堂铭·序》中直接引用:“吾闻之申包胥曰:人众者胜天,天定亦能胜人。”
朱熹在《四书或问》中指出,一个政权,如果得之非道,其寿命都不长,这就是天定胜人。其与苏轼都强调“天定”。
此后,刘过、陆游、汪藻、孙绪、髙拱、梁启超等都对“人胜天,天胜人”作过诠释,但侧重点有所不同。
在众多诠释中,对“定”“天”“胜”字的理解非常重要。
定,有安定之意。《说文》:“定,安也”。《增韻》:静也,正也,凝也,決(同决)也。这里的“定”,必然没有“一定”的意思。
天,一说天命(这在古籍中论述多涉及国家、政权的兴衰可以看出),一说自然。
胜,据现代的各种辞书,都解为“战胜”。而在冯梦龙《古今小说·裴晋公义还原配》中,具体的语境是这样的:“却又犯着恶相的,却因心地端正,肯积阴功,反祸为福。此是人定胜天,非相法之不灵也”。从这段文章可看出,“人定胜天”并无“人类一定能够战胜自然”之意,而是指在一定条件下,人的因素(心地端正、肯积阴功等)比天命更为重要。
至此,引刘禹锡《天论》中提出“天与人交相胜尔”的观点,强大的自然力能使万物生长或死亡, 是人力所不及的, 但人能明辩是非的智力技巧等也是自然力所不及的。这一观点,也应是“人定亦能胜天,天定亦能胜人”所要表达的。
至于到了近现代,“人定胜天,天定胜人”已经发生了变义,“天定胜人”已经成为消极意义而被抛弃,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“人定胜天”脱离了传统的意义而成为了定式,并长期作为激励人们改变自然、战胜自然的口号而广为传播。但是,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深入,“人一定战胜自然”的思想的局限性已被人们重新发现并发展,甚至成为了批判的对象。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是战胜与战败的关系,而应该是和谐统一的关系。
